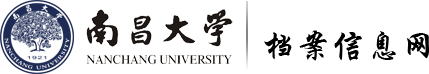-
南大记忆
怀念我的祖父何焕奎
发布时间:2017-09-29 阅读量:
抗战胜利那年我出生于乡下老家——进贤县三里乡何家,幼年时在何家生活了四年。虽然我不是长孙,却由祖父祖母带大,因为长孙大炎那时虽然也在何家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一直有外婆在身边带着,而我出生时母亲奶不够,请了奶娘,由祖母带着我,就住在1938年抗战期间祖父回乡下盖的房子里。
幼年时期这四年的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能够记得的只有很少几件事情。有一天人们从地里做完事回来,在屋前的场地上玩,我当时也在,有个人捉了一条黄鳝在我嘴巴上划了几下,说是蛇钻进我肚子里了,我吓哭了,祖母从屋里出来问是谁又在逗我,有人把我牵到祖母面前,说是捉了条黄鳝逗他玩的,祖母便哄我说化碗红糖水吃就会好,于是真给我化了一碗红糖水,我喝了也真觉得没有事了,这是我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那是一天我坐在屋里房门口玩,突然听见外面有“砰、砰”的声音,不一会儿从外面跑进来几个人,同祖母说了几句话,就架起长梯爬上阁楼,拿了几支长枪下来,又匆匆跑出去了。从大人的话里,我隐约听出大概是同别的村庄打械斗,人家打过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屋子里还有楼,上面还放了东西,我就想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屋里还有楼梯呢,也不知道楼上还有什么东西。我后来也从来没有爬上去过。我还依稀记得我们举家搬到南昌的情景,大概是1949年,走的是水路,全家分坐三条船,大伯和二伯两家各坐一条较小点的蓬船,祖父母和我父母亲等人坐一条较大些的蓬船。湖水浩淼,无边无际,我有时能够看见二伯他们的船,有时又不见他们的踪影,一次我眼看二伯坐的小船就要超过我们,还着急地要我们的大船划快点。我们到南昌后在赣江一个码头靠岸,有人搭起了跳板,父亲挽起裤腿踩在水里,扶着祖父过了跳板,又先后背着祖母和母亲趟水上岸,轮到我时,父亲干脆一只手把我夹起来送上了岸。岸上很多人,父亲说饿了,要买东西给大家吃,他在一个炸油条的小摊前,说要买炸老了的“二来子”,买后给了我一根,又香又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还有油条这样好吃的东西。
稍大一些后,我记得的事情就更多了。
我记得我由祖父祖母带到9岁,一直跟他们睡一张床。我和祖母睡一头,我睡床里边的小被窝,祖母睡外边的大被窝,祖父睡大被窝的另一头。冬天睡觉时,祖母会先让我上床,坐在大被窝里,祖父早已上床,坐在另一头。我上床后有时祖父会对祖母说:细明(我的小名)进来就热和多了。我给祖父暖过脚后,祖母也收拾好了坐上床,就让我钻进里边的小被窝。小时候早晨起来时,祖母总会先让我在她怀里坐一会儿,然后再穿衣起床。大概在我读书后就不再坐在祖母怀里了。我记得小时后吃饭就在对面我母亲房间里,每到吃饭时间,母亲就会叫我过去,吃完饭我又回到祖父祖母这边来。1954年,二伯最小的儿子大信出生,二伯的第二个儿子大仁才2岁,二伯母带不过来,就把大仁交给祖母带,于是大仁睡我的位置。从此,我搬到我弟妹的房间睡,直到1962年我17岁考上大学离开家。不过我即使不再睡在祖父祖母房间里,但不论是玩耍还是做作业,我都回到祖父祖母这边,在父母亲房间里我很不习惯。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给祖父母当小“听差”。人老之后腿脚不便,眼神不好,都想有个小孙子跟在身边,既能有个照应又可听听使唤。我是祖父母带大的,从小跟着他们睡觉,这小“听差”的事自然非我莫属。
1952年,家里当时住在南昌市中山路三道桥朝阳旅社。一天我正在门口马路上玩,看见来了一辆大马车停在门口,下来几个人,进了朝阳旅社,不一会儿祖父同他们一起出来了,祖母和其他几个长辈也跟着。祖父向祖母交代几句就上了马车,我不知道祖父为什么要坐马车,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就跟着马车追,哭喊着“公公,公公”,追了好远才被大人喊回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祖母说要带我去看公公,她提着一个竹篮牵着我,我们走了很久,来到火车站。当时我只有六七岁,跨不上火车,是列车员把我捧上去的。一上车我就闻到了一种非常诱人的香味,酸酸甜甜的,整个车厢都弥漫着。我四处张望,也没发现香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知道火车上的味道这么好闻。到了进贤县城,我们穿街过巷,来到一栋青砖大屋前。大门口有当兵的站岗,通报之后,有人来领我们进去。这是老式大屋,好几进。我们绕过两处天井,才到祖父住处。祖父看见我们显得十分高兴,祖母从篮子里拿出些鸡蛋和几罐腌菜,我则打量着房间,边看边想,原来祖父到这里来了。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窗子很大,但有许多木制小方格,光线并不很好,一张大床,挂着蚊帐,靠窗还有一张书桌,窗外是天井。祖父说这里是县公安局,他在公安局诊疗所工作,平时没事就在这个房间里看看书,也可以随便走动,有病人就来请他去。这栋房子很大,那头有好几间改做了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他主要是给犯人看看病。这么大房间就住他一个,这里的人对他都很客气,很照顾,不必记挂他。其他关着的人,就没有这么好了,都是好多人住一间,而且是地铺,有人看守。他还说如果有事要上街去也可以,不过要请假,他也没有什么事情,不会出去。祖父这些话虽然是告诉祖母的,但我在身边基本都听懂了。我们没有留宿,当天赶火车回了南昌。这大概是我记得的小时候的第一次“当差”,说是“当差”,我其实并没有做任何事,只是由祖母领到祖父那里去,让他摸摸我的头,让老人家心里感到些许宽慰而已。
祖父在进贤大约1年左右,家里每隔一两个星期都会到进贤探视一次,顺便带点换洗衣服和吃的之类。祖母去过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母亲去,细姑也去过一次,但不管是哪个大人去,每次都由我陪同,一次也没有拉过。可能每次去都特意选的星期天,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上学。每次去时,只要一进火车车厢,我就会闻到那种非常诱人的,酸酸甜甜的香味,有几次我看见列车员卖面包,有人买了吃,我怀疑可能是面包的香味但不能肯定,因为没有卖面包时,车厢里也弥漫着这种香味。这个谜底直到细姑带我去进贤探视的那次才解开。细姑在外地工作,一次回南昌探亲,让我同去进贤。我们上车不久,又有列车员过来卖面包,细姑说买个面包你吃好吗?没等我吭声,她已经从列车员手上接过一个面包给我,我一接过来几乎就肯定那诱人的香味就是这面包的味道。我撕开薄薄的透出油的包装纸,先是咬了一小口,慢慢品着,再小心翼翼掰开,里面是红红的果酱馅儿,一尝,果然酸酸甜甜的,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面包。
祖父有一首《七十自寿诗》对在进贤的这段经历有过记载,诗句后面还多处以圆括号附加了他自己的注释,这里摘录有关的两段,诗曰:“服务何妨劳改队,生涯自拟老耕农(我诊疗所以医治进贤劳改队病人为主要任务,诊所同人的生活,与各农场耕作的人一样),鼎新革故争前进,端在灵犀一点通(我自觉思想已打通,很满意现实环境)。又曰:“惊瘟监舍抬临诊(八月九日进贤完小集中各乡教育人员数百人学习有一学员赵子云患急症身死,其他各学员惊为瘟疫,发生恐惶,当晚招我往为鉴定),死颤劳囚试救营(八月十一,进贤劳改队有一劳改犯易秉照发急症人事不省手足抽搐震颤,牙关紧闭,体温高至摄氏41.5c,经打针救活),寄语妻儿无我念,人生观是为人民。”从诗中可以看出,祖父虽为江西一代名医,却能在这小小的诊疗所里,以七十高龄而救死扶伤,并且在思想上“鼎新革故”,与时代同行,实实令我感佩。当时的进贤县公安局长田博文对祖父十分敬重,后来他调南昌任江西省地质局副局长,曾两次到廉让里看望我祖父。他来我们家时我见过他,高大魁梧,方脸宽额,典型的北方人。祖父多次对我说过,田局长是个好人,也是他的恩人,在进贤时对他很照顾,这样的好人要记住。田局长在南昌工作时间不长,后来调到吉安专署任公安处处长。
祖父回南昌后,全家已经搬到廉让里7号。祖父被安排在南昌专署卫生科任职,办公地点在现在的中山路百花洲,旁边有一所医院,当时叫卫联医院。我的任务就是放学之后接祖父回家。与去进贤探望祖父不同的是,那时是大人牵着我,现在是我牵着祖父。接过几次之后,祖父担心我一个人去百花洲过马路不安全,就没让我再接,改为雇请一位姓胡的人力车夫接送,大人都叫他“老胡”,我们小孩不懂,只要见他来了就会说“老虎”来了。
后来祖父又被安排到江西省中医实验院担任西医顾问,每月工资一百零几元,当时算是高薪了。中医实验院在八一大道上(现在那里改成了南昌市卫生防疫站),离家比较远,来回不方便,院里专门给祖父一间房间休息,所以他中午从不回家,天气不好时晚上也不回来。于是我又有了新的“差事”,那就是替祖父送午饭。祖母每天中午都会准备好要送的饭,一般有两到三个菜:一个蔬菜,一个腌菜,或一小块豆腐乳。隔几天会有一个荤菜,比如豆豉烧肉、腌菜烧肉或小鱼干之类。饭菜用一个上下三层叠起的饭盒盛着,底下较深的一层盛饭,上面较浅的两层盛菜。放学之后,如果我母亲烧好了午饭,我就匆匆吃一碗,往往不等最后一口咽下,便提着饭盒出了门。如果母亲还没烧好饭,祖母就会要我先去送,让母亲留饭给我回头吃。每次送饭,我都是遵照祖母的吩咐,一路快走,片刻不停,生怕耽误时间饭菜冷了。祖父每次都准时在房间里等着我,特别是冬天,当他打开饭盒,看见冒着热气的饭菜时,总是高兴地说:好好,还是热的。当有点好菜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吃了没有,吃饱了没有,然后说他吃不了这么多,要剩几口给我。我一般都不会吃,说已经吃饱了,偶尔也有吃几口的时候。回去时祖父总是叮嘱我要小心过马路,那护犊之情终身难忘。
去进贤探望祖父和到中医实验院送饭是我小时候做得比较多的事情,此外还经常会有些临时性的“差事”,其中有几次我印象很深。
1957年大鸣大放,祖父作为社会贤达,几次应邀到省委统战部开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每次都是我负责接送。我以前曾经陪祖父出席过几次座谈会,会上人们谈笑风生,还有花生瓜子橘子等,但是这几次好象比较严肃,而且只有茶水没有点心,家人也不能陪同。记得开会的地方是一栋很大很长的楼,会议室在二楼。有一次祖父只让我送到会议室门口,还有一次让我送进了会议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中间是会议桌,摆成一圈,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围坐了许多人。进去后就有人过来迎接,问明身份后便让我在外面等候,说过两三个小时再来接。我一直看着那人很客气地小心翼翼地把祖父扶引到座位上,便到外面的走廊上一直等到祖父出来。祖父回家后告诉我,会议期间,省委领导曾两次很客气地对他说,你老人家怎么不发言?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吗?如果有可以提出来。祖父说:“我什么意见也没有提,我对他说共产党待我不薄,我对现在的社会很满意,我没有意见。”这的确是祖父的大实话,他早在1952年写的《七十自寿诗》中就曾表示过“我自觉思想已打通,很满意现实环境”。像祖父这样一向很知足的人,在那个年代共产党还能用他一技之长,得以在古稀之年领一份公薪,当然很满意。所幸正是他的大实话,使他后来躲过反右一劫,也许真的是老实人不吃亏吧。那年我12岁,这是我当过的最重要的“差事”。
大概是1958年,胡先骕先生到江西来讲学。祖父说要和胡先骕吃饭,我也没听清究竟是谁请谁。那天祖父很高兴,也很慎重其事,在家里等候,他说胡先骕是中国有名的植物分类学家,难得回江西一次,他们很久没见面了。过了一会胡先骕先生来到廉让里我们家,祖父迎出大门,胡先骕先生忙上前扶住祖父说不必这样客气。在我记忆中,胡先骕先生中等身材,长方脸,上唇好像留有短须,小分头。他们在祖父房间里说了会儿话,然后起身说要去外面什么饭店吃饭,胡先骕先生出客厅下台阶时,祖父让我扶着胡先骕先生,胡先生反过来要我扶着祖父。这次没让我陪同出去,只在家里大门口送客,是我最简单的一次“外事”任务。
我曾经错过一次“美差”,说是“美差”,其实是祖母对我平时“听差”较多的一次犒赏,我却没有领会她老人家一番美意。那次是梅兰芳到南昌演出,祖母有两张票要带我去。我照例问去哪,做什么。当听说是去看戏,我就说不想去,带别人去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我不能拒绝,但带我去看戏这明摆着是件美事,把这等美事让给别人应该不会怪罪于我的,祖母便带丽娟去了。后来我每想起这事就后悔不已,竟然主动放弃了一睹梅大师风采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还有一次我“严重失职”。好像那是1958年,省卫生厅长刘之纲续弦之喜,祖父和祖母应邀去他家喝喜酒,我自然随行。到了晚上,祖母要回家,而祖父想在好友家多留一会儿。刘公公是祖父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两人是执友,平时难得相聚,见面话多,也是常情。我不能分身,只能陪一个,祖父便让我跟祖母先走,刘公公也说他会派人送的。正当我们在家等待祖父回来的时候,有人来报信说祖父掉进东湖里了,人已送医院。家人赶紧接回祖父,只见他摔得鼻青脸肿,搽了好多红药水。原来他从刘公公家出来时,执意不让人送,说自己一人能够慢慢走回家。当时他正走在人行道上,右边就是东湖,忽然听见有汽车喇叭声,由于当时路灯昏暗,他眼睛又不好,没看清楚,以为自己走在马路上,便往右让了几步,一下就掉进湖里。所幸当时东湖正清理淤泥,前一天湖水已经抽干,几尺厚的淤泥正待挖运,祖父这才得以“软着陆”,有惊无险,只受了些表皮外伤,筋骨没有大碍。祖母很后悔,如果当时留我下来陪祖父就不会有事了。
我上初中后,祖父经常对我说:你要攒劲读书,不读好书就没有出息。在我的印象中,祖父虽然没有怎么具体过问我的学习,但他总是以身作则,用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着我。
祖父年轻时是怎么刻苦求学的我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过我。他只说过那时候条件很差,晚上只能点盏小油灯,有时为了省油,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的时候,连这盏小油灯也舍不得点,只能就着暮色,还有时甚至要借着月光读书。我想祖父的眼睛为什么在50多岁以后就坏了,恐怕与他年轻时刻苦读书而没有条件保护好眼睛不无关系。倒是祖母给我讲过祖父小时读书的故事,那时祖父家里穷,读不起私塾,他在外面放牛时,常常会到另外一个村庄的财主家私塾去,趴在人家窗口上看,去的次数多了以后,有时还会在窗口偷偷教财主的儿子写文章。私塾先生就让祖父读书给他听,发现祖父确实很聪明,就同意免费教祖父读书,让他和那财主家的儿子做伴。
但是,祖父晚年学习之刻苦是我时时目睹的,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医学事业的追求。他眼睛高度近视,看书时需要在阳光或灯光下面脸贴着书才能看清,写东西时也是这样,脸几乎要贴着纸面。可以想见一个老人眼神不好,再加上写字时手还常哆嗦,读书写字要比年轻人多付出多少艰辛。祖父70岁以后应用巴甫洛夫神经病理学学说来研究我国中医理论,撰写了许多论文。为了更准确理解巴甫洛夫学说,他不满足于只看巴甫洛夫著作的译文,还要阅读巴甫洛夫的俄文原版著作。祖父精通日语和德语自不待言,但以前并不懂俄语,是为了研究巴甫洛夫学说才自学俄语,由于条件所限他只能借助字典来学,能看不能读。1959年我上高中,开始学俄语,他得知后很高兴,让我把俄语每个字母的发音读给他听,还特别让我教他发俄语“p”的音,又念一些单词给我听看是否正确。我怕他老人家还会向我提别的什么问题,当时偷偷“恶补”了一段时间俄语。祖父硬是在这种情况下读了大量巴甫洛夫的有关著作和中医书籍,撰写了不少论文,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我至今还保留着祖父的《从巴甫洛夫学说研究失语症病例的治愈机制》部分手稿。
祖父参加辛亥革命的事,我小时略有所闻。祖父曾经对我说过,他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也许这对于祖父来说只是他年轻时的遥远回忆吧,详细情况他对我说得不多,我也记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他说过广州起义他本来是要回国参加的,后来因为要留下搞宣传而没有去成,如果他去了,也许就会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一个了。祖父还给我讲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故事,当讲到袁世凯没有当多久皇帝就下台时,他自己就会笑起来。后来父亲告诉我,祖父曾经说过千叶医科学校有一块纪念碑,纪念辛亥革命时留学生回国参加战地救护以及校长捐资购药支持留学生回国的事迹,是他写的碑文,另请人刻的。
1978年,我偶然在《参考消息》上看见一则报道,题为《日本千叶县发现我辛亥革命时留日学生纪念碑》,我立刻把此事告诉父亲,并且给了他这份报纸的复印件,原件我自己保留着,是1978年10月15日的《参考消息》。据报导,纪念碑埋在千叶医学部附属医院一处花园的泥土里,当时只露出一角,千叶大学考古学教授相川日出雄在和旅居千叶的华侨陈赞、金克强散步时,那露出的一角被相川先生偶然踢到,纪念碑因此才被发现。
纪念碑高约2公尺,宽约80公分。正面上方由右至左用阳文刻了“纪念碑”三个篆字。下面用阴文的正楷刻的碑文,全文为:
“辛亥秋中华民国革命事起武汉南北军战争甚烈同学恐战祸蔓延而伤亡之数多也乃集同志起红十字队连合留日医药学生全体返国以图拯救时本校校长刘先生深韪斯议凡关于救伤看护法悉心指导各学友复醵资购药为赠临歧殷殷益资策励同仁返国分驻于湘汉江淮间伤兵颇利赖之六阅月战局告终蒇事返校虽无善可纪而刘先生及诸学友盛弗可泯也爰种树立碑以为纪念,其辞曰:王纲解纽 共和初建 国步艰难 兵戎数见 伏尸塞川 碧血膏野 怎此民生 谁大护者 壮三军气 红十字旗 生死肉骨 拯难扶危 维列先生 亦越诸友 作则大同 跻世仁寿 人道张皇 德意滂沛 木石万年 永垂勿替
中华民国留学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生同建”
碑的反面刻着:“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九日
日本大正元年十一月九日”
1999年,韵娟的女儿华峻在美国留学暑假回国探亲,她遵我父亲嘱咐,途经日本东京时特意绕道千叶访过此碑。华峻回国后给了我一张千叶医科大学报道此事的报纸复印件。
我想祖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应该是他人生中光彩的一页。
祖父是1960年去世的。那年我15岁,正读高中一年级,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记得祖父去世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躺在床上,很少饮食,祖母也十分焦虑,一天她叮嘱我说:“这些天公公不太行了,你放了学就早点回家。”所以那段时间只要学校没有课,我就赶紧回家。我不知道祖父得的什么病,只是从大人们凝重而焦虑的神情中感觉到祖父病得很重。那些日子我整天心事重重,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担心着祖父。恰逢当时南昌市修建青山路,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几天义务劳动,去工地挑土方。工地离家好几里路,我怕万一有什么事情一时赶不回来,所以那几天早晨临行前都要到祖父床前看看,告诉他我要去劳动了,等他老人家点过头之后我才走。祖父去世那天一大早我又去祖父的房间,见他老人家闭着眼睛安详地躺着,我不忍打扰,便轻声告诉祖母,她说你去吧,早点回来。在工地上我一边挑土一边盼着早点收工,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心里一阵紧,我问老师几点了,得知已经10点多钟,心里越来越不安,好不容易才盼到11点宣布收工。我三步并两步一路小跑回家,不知道为什么越接近家里越心慌,快到家时我抬头一看,房前屋后已经聚着不少人正在窃窃私语,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明白,自己日夜担心却又不敢去想的事终于临头。我分开人群,也没有理会人们的目光,几乎是跑进屋里,冲过后客厅,跨过前客厅,扑进祖父房间。里面已经有好几位长辈, 只听祖母一声哭:“细明你回来了,公公过了,给公公磕头。”我应声跪下,趴在祖父床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老人家削瘦的脸庞,摸着他冰凉蜡黄的额头,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我呼唤着“公公,公公!” 我明知不可能但还是想让他老人家听见,我不愿相信我朝夕相依的最亲的亲人就这样撒手人寰!祖母和二伯母把我搀起,祖母告诉我:“公公是上午10点多钟去世的,你走后不久他就醒了,还问过几次细明来了没有,我告诉他你去劳动了,已经来打过招呼了。”人们常说,亲人之间会有一种心灵感应,祖父去世的那一刻,正是我在青山路挑土方时,心里突然掠过不祥,强烈感到不安的时候,难道这是祖父在和我永别吗?难道这是我感觉到了祖父心灵的呼唤吗?我真后悔去青山路劳动,我应该请假守在祖父身边的,可是我当时哪敢请假?何况我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像往常一样回来还能看见他老人家安详地躺在床上,甚至希望会有奇迹发生,他老人家会慢慢好起来。祖父之死,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可是现在,除了我的后悔,我的悲泣,除了后来与我相伴的无尽回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祖父病重期间,刘公公和江西中医实验院院长姚荷生等几位名医都先后来家里探视和为他治疗过,两次我都正好在场。刘公公来时祖父挣扎着要起身,刘公公不让,自己俯身坐在床头,祖父无力地摇摇头说“我不行了”刘公公便安慰着,两人小声谈了好一会。姚荷生是同两位中医一起来的,他们询问了祖父的病情,为他号过脉,还开了药方,告辞之前又同祖母小声交谈着什么,只听祖母说,“他不肯吃药。”后来我想祖父一定是了解自己的病情,自觉病入膏肓,所以后期拒绝服药。
我一直想知道祖父得的是什么病,多年以后我问过父亲,他也说不出来,因为他1958年下放去了赣南,一直不在家,是在祖父死后才奔丧的。但父亲对我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祖父之死,与家里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一件事是大伯1959年蒙受不白之冤,离开了南昌三中,被强送劳动教养 。大伯是祖父的长子,最受器重,祖父曾经对他寄予厚望,大伯出事,对祖父打击很大。第二件事是1960年国家实行精简职工队伍政策,祖父因此办了退职。退职不同于退休,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退休金,退职只能一次性拿一笔退职费,以后国家就再不管你。我不知道祖父得了多少退职费,但我知道他每月一百零几元的薪水再也没有了。
祖父一向很达观,他在农村老家的产业被没收,南昌城里中山路的房子变卖后所得款项也悉数捐给老家乡下,六眼井的房子被社会主义改造,仅剩廉让里7号一栋自住房,这些他都豁然处之,对前途都没有失去过信心。可是现在年近八旬,却从此失去经济来源,再加上没有工作的祖母和疯子二姑,家庭竟然遭遇如此变故,这对于一个身患重病的垂暮老人,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我想祖父之死,除了因为他得病以外,的确与他生命最后一年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有很大关系。